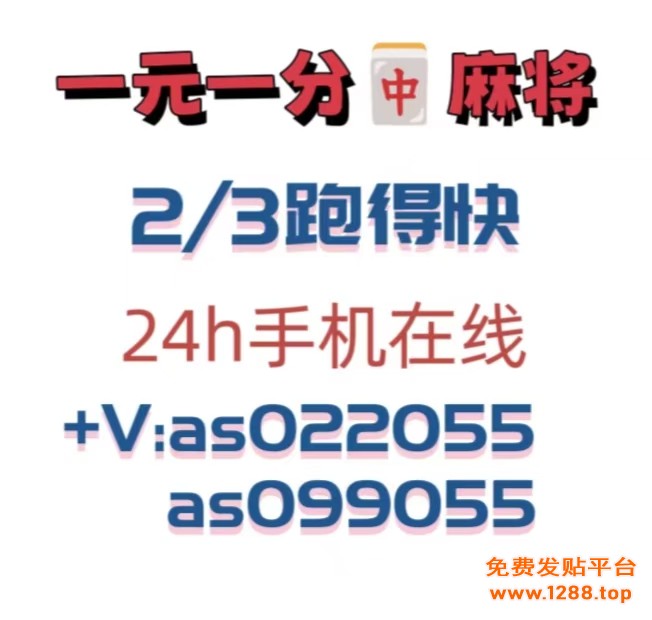 我在家的时候,我指的是我小学至中学这一段时间。家里经常生病的有两个人,一个是我奶奶一个就是我。我奶奶人老多病,是正常现象,而我年小多病,与体弱有关。母亲生我那年,刚好四十岁,老来得子,想着法子吃点补的,听人家说云南白药掺进母鸡汤里煲吃了补血。结果吃多,虚火内炽,脸色潮红,浑身像高烧的一样,胃口很差,就又按土郎中黄三的说法,吃了朱砂、黄连、地黄、当归、甘草五味药,败了虚火,安了神。可是,我遭了罪,先是跟着上火,然后就是泄个不停(吃奶故)。从此落下病根,平时虚火旺炽,胃口差,一着凉就会闹肚子。那时,家里的药罐子经常是满的,炖完奶奶的药汤就轮到我的了。黄三的药铺里多的是黄连,我买的多的药就是黄连和熟地,光吃黄连伤脾胃,加点熟地就好了。黄三大名我不清楚,知道他家是郎中世家,他父亲传给了他,因为他的两个哥哥都不肯学做郎中。黄三就成了江夏堂的继承人,这里需要交待的是,江夏是黄姓宗祠号,药铺起了××堂,是传统的习惯。 我低着头,不敢往前看,我在心里祈求老师不要再打他了。我只感觉到我恨自己,可是也恨他!我恨他不该那么倔强!我在心里说:你在地上跪一会,老师消了气不就没事了嘛!为什么偏象是头上长角了似的! 几个老外在翻译的带领下,走进这个院子,和我们一起看着朱红的大门,看着照壁上的图画。这些画源自哪个年代,已无从考据,只是孔子后裔的诸多故事,被日益生动地流传下来。那些老外一付虔诚的样子,认真地看,似懂非懂地听。我在怀疑他们的同时,又谴责了自己的浅薄。倘若我站在卢浮宫,是不是也被人称为槛外人?但凡是跨进这个大院的人,是怀着对孔子及其后人尊崇之心的。一种潜在的隐秘的文化纽带,把不同地方、肤色、语言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。他或她,还有我,在这个院子中静气屏息蹑足行走。先人早已不在,但不灭的灵魂在文化的时空中漫游。如果我们愿意想象,孔子的后人,在这里或那里看书、著书,烟火气息的生活。夜晚,一豆灯火之下,他们把头勾得很低,在书简之中,写下自己的思想。一些明明灭灭、虚虚实实的故事,在这里展开,让我迷惑。是的,迷惑。这种迷惑是因了时空的阻隔,而这种迷惑却因着特殊的地方,有了不可辩驳的可能性。这就是这个院子不断吸引人前来的魅力所在。 《美文》,1992年9月创刊,创刊时为韵文季刊,2001年兴盛为半季刊。下半季刊是“妙龄韵文”,公布中弟子韵文大作。《美文》有17篇大作收入国度成天制国学语文讲义和课本。个中有15篇为中弟子作家。 />英雄崮 在沂蒙山区,有很多形状特殊的山,这些山山峰陡峭,但山顶浑圆,地貌学上称“方山”,俗称崮。沂蒙山区有著名的72崮,其中我们蒙阴就有36座,而我的老家在一个偏远的山镇--岱崮,此地更因崮多而闻名。 我的童年就是在一座崮下度过的,那山崮的名字叫板崮。小时候,我经常和小朋友们去爬山。山就在我们家门口,又不是太高,一天一个来回也黑不了天,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壮举了。因为老人们常讲,板崮山曾是抗日根据地,那里死过好多革命战士、逃难的老百姓,也有被打死的日本鬼子、汉奸,特别是山头上和山洞里,曾经血流成河,所以传说那里有许多鬼魂,小孩子去了,会做恶梦的。我们几个女孩子从没有进过山洞,据说那就是当年的防空洞。有一次,几个胆大的男孩偏不信邪,点着松枝,吆三喝四地像英雄一样地走进去,不知谁在里面尖叫了一声,他们就风一样地跑出来,出来就笑作一团,说是什么也没看到。 这小小的恐惧很快就过去了。女孩子走那条陡窄的小路爬到山顶,男孩子就从比较容易爬的地方攀岩上去,也有爬不上去的,就成为大家的笑柄。山顶上有倒塌的房子,有的墙体还残破地站立着,大人们说的没错,的确是有人住过。“看!”谁又发现了几块黑瓷碗片,这又证实了山顶上住人的可能性,也让我们想起了那个洞和鬼魂的传说,还真有些害怕,于是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走到离洞远一点的地方玩。我们经常在这里玩打仗的游戏,体验一下“战争”的感觉。第二天我们见面的时候,第一句话就是问做恶梦了吗?没人应声,于是大家就对大人们的话产生了怀疑,对鬼魂的说法也不觉得可信了。有一男孩说:可能是鬼魂也有好坏,鬼魂害怕抗日英雄的英魂,不敢作乱了。这一说法,得到我们一致的认同。 二十多年后,我给小儿讲了童年的故事并告诉他此山曾是战场,小儿持怀疑态度,非要亲自去认定一下。在山顶上,他看到了破碎的碗片,废弃的石碾,倒塌的院墙等等,才吐出一句:看来还真打过仗啊!看到他惊奇的样子,我想到了那句话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那曾经的一切,对于他,的确是太遥远了,以后我要多给他讲讲这方面的故事。 其实,在我们岱崮曾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。最著名的莫过于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了。1943年11月1日,日伪军1万余人合击沂蒙山抗日根据地,我军指战员们依托山崮天险沉着应战,当地民众也送粮送水,支援守崮战斗。经过15天的浴血奋战,胜利地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,参战将士被授予“岱崮连”称号。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,还有第二次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、“龙须崮暴动”等,我就不一一赘述了。 我的故乡板崮山,它曾是抗日战争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之一,虽然它不像“孟良崮战役”那样惊天动地,也不像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那样轰轰烈烈,却随时随地地削弱了鬼子的力量。因为这些山崮的易守难攻,让鬼子们胆战心惊、四面楚歌,以至于屡次错失战机,这样一来,就更加快了我军胜利的步伐。从这一点上来说,板崮山、大崮、龙须崮等,都曾经是抗日英雄并肩作战的“战友”!今天,这些崮们经受了几十年风雨的洗礼,依旧赫然地屹立着。 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,如果没有英雄们的流血牺牲,哪来我们今天的幸福呢?英雄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,在他们为之战斗的地方,子孙后代们正奋斗着、努力着,把他们的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。人们越来越好的生活,也许可以告慰那些逝去的英魂吧!我们--这些英雄的后辈们,除了把家乡建设得更好,别无选择!
我在家的时候,我指的是我小学至中学这一段时间。家里经常生病的有两个人,一个是我奶奶一个就是我。我奶奶人老多病,是正常现象,而我年小多病,与体弱有关。母亲生我那年,刚好四十岁,老来得子,想着法子吃点补的,听人家说云南白药掺进母鸡汤里煲吃了补血。结果吃多,虚火内炽,脸色潮红,浑身像高烧的一样,胃口很差,就又按土郎中黄三的说法,吃了朱砂、黄连、地黄、当归、甘草五味药,败了虚火,安了神。可是,我遭了罪,先是跟着上火,然后就是泄个不停(吃奶故)。从此落下病根,平时虚火旺炽,胃口差,一着凉就会闹肚子。那时,家里的药罐子经常是满的,炖完奶奶的药汤就轮到我的了。黄三的药铺里多的是黄连,我买的多的药就是黄连和熟地,光吃黄连伤脾胃,加点熟地就好了。黄三大名我不清楚,知道他家是郎中世家,他父亲传给了他,因为他的两个哥哥都不肯学做郎中。黄三就成了江夏堂的继承人,这里需要交待的是,江夏是黄姓宗祠号,药铺起了××堂,是传统的习惯。 我低着头,不敢往前看,我在心里祈求老师不要再打他了。我只感觉到我恨自己,可是也恨他!我恨他不该那么倔强!我在心里说:你在地上跪一会,老师消了气不就没事了嘛!为什么偏象是头上长角了似的! 几个老外在翻译的带领下,走进这个院子,和我们一起看着朱红的大门,看着照壁上的图画。这些画源自哪个年代,已无从考据,只是孔子后裔的诸多故事,被日益生动地流传下来。那些老外一付虔诚的样子,认真地看,似懂非懂地听。我在怀疑他们的同时,又谴责了自己的浅薄。倘若我站在卢浮宫,是不是也被人称为槛外人?但凡是跨进这个大院的人,是怀着对孔子及其后人尊崇之心的。一种潜在的隐秘的文化纽带,把不同地方、肤色、语言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。他或她,还有我,在这个院子中静气屏息蹑足行走。先人早已不在,但不灭的灵魂在文化的时空中漫游。如果我们愿意想象,孔子的后人,在这里或那里看书、著书,烟火气息的生活。夜晚,一豆灯火之下,他们把头勾得很低,在书简之中,写下自己的思想。一些明明灭灭、虚虚实实的故事,在这里展开,让我迷惑。是的,迷惑。这种迷惑是因了时空的阻隔,而这种迷惑却因着特殊的地方,有了不可辩驳的可能性。这就是这个院子不断吸引人前来的魅力所在。 《美文》,1992年9月创刊,创刊时为韵文季刊,2001年兴盛为半季刊。下半季刊是“妙龄韵文”,公布中弟子韵文大作。《美文》有17篇大作收入国度成天制国学语文讲义和课本。个中有15篇为中弟子作家。 />英雄崮 在沂蒙山区,有很多形状特殊的山,这些山山峰陡峭,但山顶浑圆,地貌学上称“方山”,俗称崮。沂蒙山区有著名的72崮,其中我们蒙阴就有36座,而我的老家在一个偏远的山镇--岱崮,此地更因崮多而闻名。 我的童年就是在一座崮下度过的,那山崮的名字叫板崮。小时候,我经常和小朋友们去爬山。山就在我们家门口,又不是太高,一天一个来回也黑不了天,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壮举了。因为老人们常讲,板崮山曾是抗日根据地,那里死过好多革命战士、逃难的老百姓,也有被打死的日本鬼子、汉奸,特别是山头上和山洞里,曾经血流成河,所以传说那里有许多鬼魂,小孩子去了,会做恶梦的。我们几个女孩子从没有进过山洞,据说那就是当年的防空洞。有一次,几个胆大的男孩偏不信邪,点着松枝,吆三喝四地像英雄一样地走进去,不知谁在里面尖叫了一声,他们就风一样地跑出来,出来就笑作一团,说是什么也没看到。 这小小的恐惧很快就过去了。女孩子走那条陡窄的小路爬到山顶,男孩子就从比较容易爬的地方攀岩上去,也有爬不上去的,就成为大家的笑柄。山顶上有倒塌的房子,有的墙体还残破地站立着,大人们说的没错,的确是有人住过。“看!”谁又发现了几块黑瓷碗片,这又证实了山顶上住人的可能性,也让我们想起了那个洞和鬼魂的传说,还真有些害怕,于是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走到离洞远一点的地方玩。我们经常在这里玩打仗的游戏,体验一下“战争”的感觉。第二天我们见面的时候,第一句话就是问做恶梦了吗?没人应声,于是大家就对大人们的话产生了怀疑,对鬼魂的说法也不觉得可信了。有一男孩说:可能是鬼魂也有好坏,鬼魂害怕抗日英雄的英魂,不敢作乱了。这一说法,得到我们一致的认同。 二十多年后,我给小儿讲了童年的故事并告诉他此山曾是战场,小儿持怀疑态度,非要亲自去认定一下。在山顶上,他看到了破碎的碗片,废弃的石碾,倒塌的院墙等等,才吐出一句:看来还真打过仗啊!看到他惊奇的样子,我想到了那句话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那曾经的一切,对于他,的确是太遥远了,以后我要多给他讲讲这方面的故事。 其实,在我们岱崮曾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。最著名的莫过于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了。1943年11月1日,日伪军1万余人合击沂蒙山抗日根据地,我军指战员们依托山崮天险沉着应战,当地民众也送粮送水,支援守崮战斗。经过15天的浴血奋战,胜利地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,参战将士被授予“岱崮连”称号。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,还有第二次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、“龙须崮暴动”等,我就不一一赘述了。 我的故乡板崮山,它曾是抗日战争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之一,虽然它不像“孟良崮战役”那样惊天动地,也不像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那样轰轰烈烈,却随时随地地削弱了鬼子的力量。因为这些山崮的易守难攻,让鬼子们胆战心惊、四面楚歌,以至于屡次错失战机,这样一来,就更加快了我军胜利的步伐。从这一点上来说,板崮山、大崮、龙须崮等,都曾经是抗日英雄并肩作战的“战友”!今天,这些崮们经受了几十年风雨的洗礼,依旧赫然地屹立着。 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,如果没有英雄们的流血牺牲,哪来我们今天的幸福呢?英雄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,在他们为之战斗的地方,子孙后代们正奋斗着、努力着,把他们的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。人们越来越好的生活,也许可以告慰那些逝去的英魂吧!我们--这些英雄的后辈们,除了把家乡建设得更好,别无选择!推荐麻将群--红中麻将一元一分群--将影
2025-04-05 07:47 浏览:1
加微信【as099055或as011033或as022055或Q号675434346】周末一起玩红中麻将亲友圈一元一分和跑得快,手机app俱乐部里打,亲友圈内结算加不上微信就加QQ:675434346如果添加频繁就换一个加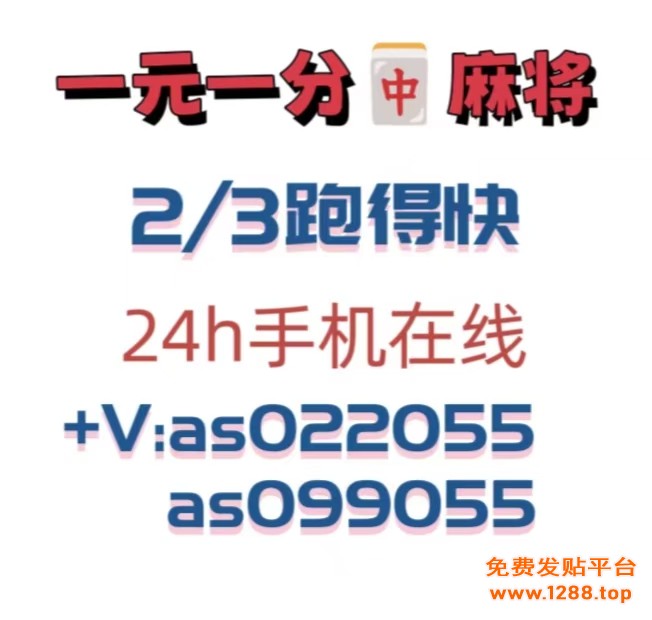 我在家的时候,我指的是我小学至中学这一段时间。家里经常生病的有两个人,一个是我奶奶一个就是我。我奶奶人老多病,是正常现象,而我年小多病,与体弱有关。母亲生我那年,刚好四十岁,老来得子,想着法子吃点补的,听人家说云南白药掺进母鸡汤里煲吃了补血。结果吃多,虚火内炽,脸色潮红,浑身像高烧的一样,胃口很差,就又按土郎中黄三的说法,吃了朱砂、黄连、地黄、当归、甘草五味药,败了虚火,安了神。可是,我遭了罪,先是跟着上火,然后就是泄个不停(吃奶故)。从此落下病根,平时虚火旺炽,胃口差,一着凉就会闹肚子。那时,家里的药罐子经常是满的,炖完奶奶的药汤就轮到我的了。黄三的药铺里多的是黄连,我买的多的药就是黄连和熟地,光吃黄连伤脾胃,加点熟地就好了。黄三大名我不清楚,知道他家是郎中世家,他父亲传给了他,因为他的两个哥哥都不肯学做郎中。黄三就成了江夏堂的继承人,这里需要交待的是,江夏是黄姓宗祠号,药铺起了××堂,是传统的习惯。 我低着头,不敢往前看,我在心里祈求老师不要再打他了。我只感觉到我恨自己,可是也恨他!我恨他不该那么倔强!我在心里说:你在地上跪一会,老师消了气不就没事了嘛!为什么偏象是头上长角了似的! 几个老外在翻译的带领下,走进这个院子,和我们一起看着朱红的大门,看着照壁上的图画。这些画源自哪个年代,已无从考据,只是孔子后裔的诸多故事,被日益生动地流传下来。那些老外一付虔诚的样子,认真地看,似懂非懂地听。我在怀疑他们的同时,又谴责了自己的浅薄。倘若我站在卢浮宫,是不是也被人称为槛外人?但凡是跨进这个大院的人,是怀着对孔子及其后人尊崇之心的。一种潜在的隐秘的文化纽带,把不同地方、肤色、语言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。他或她,还有我,在这个院子中静气屏息蹑足行走。先人早已不在,但不灭的灵魂在文化的时空中漫游。如果我们愿意想象,孔子的后人,在这里或那里看书、著书,烟火气息的生活。夜晚,一豆灯火之下,他们把头勾得很低,在书简之中,写下自己的思想。一些明明灭灭、虚虚实实的故事,在这里展开,让我迷惑。是的,迷惑。这种迷惑是因了时空的阻隔,而这种迷惑却因着特殊的地方,有了不可辩驳的可能性。这就是这个院子不断吸引人前来的魅力所在。 《美文》,1992年9月创刊,创刊时为韵文季刊,2001年兴盛为半季刊。下半季刊是“妙龄韵文”,公布中弟子韵文大作。《美文》有17篇大作收入国度成天制国学语文讲义和课本。个中有15篇为中弟子作家。 />英雄崮 在沂蒙山区,有很多形状特殊的山,这些山山峰陡峭,但山顶浑圆,地貌学上称“方山”,俗称崮。沂蒙山区有著名的72崮,其中我们蒙阴就有36座,而我的老家在一个偏远的山镇--岱崮,此地更因崮多而闻名。 我的童年就是在一座崮下度过的,那山崮的名字叫板崮。小时候,我经常和小朋友们去爬山。山就在我们家门口,又不是太高,一天一个来回也黑不了天,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壮举了。因为老人们常讲,板崮山曾是抗日根据地,那里死过好多革命战士、逃难的老百姓,也有被打死的日本鬼子、汉奸,特别是山头上和山洞里,曾经血流成河,所以传说那里有许多鬼魂,小孩子去了,会做恶梦的。我们几个女孩子从没有进过山洞,据说那就是当年的防空洞。有一次,几个胆大的男孩偏不信邪,点着松枝,吆三喝四地像英雄一样地走进去,不知谁在里面尖叫了一声,他们就风一样地跑出来,出来就笑作一团,说是什么也没看到。 这小小的恐惧很快就过去了。女孩子走那条陡窄的小路爬到山顶,男孩子就从比较容易爬的地方攀岩上去,也有爬不上去的,就成为大家的笑柄。山顶上有倒塌的房子,有的墙体还残破地站立着,大人们说的没错,的确是有人住过。“看!”谁又发现了几块黑瓷碗片,这又证实了山顶上住人的可能性,也让我们想起了那个洞和鬼魂的传说,还真有些害怕,于是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走到离洞远一点的地方玩。我们经常在这里玩打仗的游戏,体验一下“战争”的感觉。第二天我们见面的时候,第一句话就是问做恶梦了吗?没人应声,于是大家就对大人们的话产生了怀疑,对鬼魂的说法也不觉得可信了。有一男孩说:可能是鬼魂也有好坏,鬼魂害怕抗日英雄的英魂,不敢作乱了。这一说法,得到我们一致的认同。 二十多年后,我给小儿讲了童年的故事并告诉他此山曾是战场,小儿持怀疑态度,非要亲自去认定一下。在山顶上,他看到了破碎的碗片,废弃的石碾,倒塌的院墙等等,才吐出一句:看来还真打过仗啊!看到他惊奇的样子,我想到了那句话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那曾经的一切,对于他,的确是太遥远了,以后我要多给他讲讲这方面的故事。 其实,在我们岱崮曾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。最著名的莫过于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了。1943年11月1日,日伪军1万余人合击沂蒙山抗日根据地,我军指战员们依托山崮天险沉着应战,当地民众也送粮送水,支援守崮战斗。经过15天的浴血奋战,胜利地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,参战将士被授予“岱崮连”称号。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,还有第二次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、“龙须崮暴动”等,我就不一一赘述了。 我的故乡板崮山,它曾是抗日战争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之一,虽然它不像“孟良崮战役”那样惊天动地,也不像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那样轰轰烈烈,却随时随地地削弱了鬼子的力量。因为这些山崮的易守难攻,让鬼子们胆战心惊、四面楚歌,以至于屡次错失战机,这样一来,就更加快了我军胜利的步伐。从这一点上来说,板崮山、大崮、龙须崮等,都曾经是抗日英雄并肩作战的“战友”!今天,这些崮们经受了几十年风雨的洗礼,依旧赫然地屹立着。 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,如果没有英雄们的流血牺牲,哪来我们今天的幸福呢?英雄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,在他们为之战斗的地方,子孙后代们正奋斗着、努力着,把他们的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。人们越来越好的生活,也许可以告慰那些逝去的英魂吧!我们--这些英雄的后辈们,除了把家乡建设得更好,别无选择!
我在家的时候,我指的是我小学至中学这一段时间。家里经常生病的有两个人,一个是我奶奶一个就是我。我奶奶人老多病,是正常现象,而我年小多病,与体弱有关。母亲生我那年,刚好四十岁,老来得子,想着法子吃点补的,听人家说云南白药掺进母鸡汤里煲吃了补血。结果吃多,虚火内炽,脸色潮红,浑身像高烧的一样,胃口很差,就又按土郎中黄三的说法,吃了朱砂、黄连、地黄、当归、甘草五味药,败了虚火,安了神。可是,我遭了罪,先是跟着上火,然后就是泄个不停(吃奶故)。从此落下病根,平时虚火旺炽,胃口差,一着凉就会闹肚子。那时,家里的药罐子经常是满的,炖完奶奶的药汤就轮到我的了。黄三的药铺里多的是黄连,我买的多的药就是黄连和熟地,光吃黄连伤脾胃,加点熟地就好了。黄三大名我不清楚,知道他家是郎中世家,他父亲传给了他,因为他的两个哥哥都不肯学做郎中。黄三就成了江夏堂的继承人,这里需要交待的是,江夏是黄姓宗祠号,药铺起了××堂,是传统的习惯。 我低着头,不敢往前看,我在心里祈求老师不要再打他了。我只感觉到我恨自己,可是也恨他!我恨他不该那么倔强!我在心里说:你在地上跪一会,老师消了气不就没事了嘛!为什么偏象是头上长角了似的! 几个老外在翻译的带领下,走进这个院子,和我们一起看着朱红的大门,看着照壁上的图画。这些画源自哪个年代,已无从考据,只是孔子后裔的诸多故事,被日益生动地流传下来。那些老外一付虔诚的样子,认真地看,似懂非懂地听。我在怀疑他们的同时,又谴责了自己的浅薄。倘若我站在卢浮宫,是不是也被人称为槛外人?但凡是跨进这个大院的人,是怀着对孔子及其后人尊崇之心的。一种潜在的隐秘的文化纽带,把不同地方、肤色、语言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。他或她,还有我,在这个院子中静气屏息蹑足行走。先人早已不在,但不灭的灵魂在文化的时空中漫游。如果我们愿意想象,孔子的后人,在这里或那里看书、著书,烟火气息的生活。夜晚,一豆灯火之下,他们把头勾得很低,在书简之中,写下自己的思想。一些明明灭灭、虚虚实实的故事,在这里展开,让我迷惑。是的,迷惑。这种迷惑是因了时空的阻隔,而这种迷惑却因着特殊的地方,有了不可辩驳的可能性。这就是这个院子不断吸引人前来的魅力所在。 《美文》,1992年9月创刊,创刊时为韵文季刊,2001年兴盛为半季刊。下半季刊是“妙龄韵文”,公布中弟子韵文大作。《美文》有17篇大作收入国度成天制国学语文讲义和课本。个中有15篇为中弟子作家。 />英雄崮 在沂蒙山区,有很多形状特殊的山,这些山山峰陡峭,但山顶浑圆,地貌学上称“方山”,俗称崮。沂蒙山区有著名的72崮,其中我们蒙阴就有36座,而我的老家在一个偏远的山镇--岱崮,此地更因崮多而闻名。 我的童年就是在一座崮下度过的,那山崮的名字叫板崮。小时候,我经常和小朋友们去爬山。山就在我们家门口,又不是太高,一天一个来回也黑不了天,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壮举了。因为老人们常讲,板崮山曾是抗日根据地,那里死过好多革命战士、逃难的老百姓,也有被打死的日本鬼子、汉奸,特别是山头上和山洞里,曾经血流成河,所以传说那里有许多鬼魂,小孩子去了,会做恶梦的。我们几个女孩子从没有进过山洞,据说那就是当年的防空洞。有一次,几个胆大的男孩偏不信邪,点着松枝,吆三喝四地像英雄一样地走进去,不知谁在里面尖叫了一声,他们就风一样地跑出来,出来就笑作一团,说是什么也没看到。 这小小的恐惧很快就过去了。女孩子走那条陡窄的小路爬到山顶,男孩子就从比较容易爬的地方攀岩上去,也有爬不上去的,就成为大家的笑柄。山顶上有倒塌的房子,有的墙体还残破地站立着,大人们说的没错,的确是有人住过。“看!”谁又发现了几块黑瓷碗片,这又证实了山顶上住人的可能性,也让我们想起了那个洞和鬼魂的传说,还真有些害怕,于是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走到离洞远一点的地方玩。我们经常在这里玩打仗的游戏,体验一下“战争”的感觉。第二天我们见面的时候,第一句话就是问做恶梦了吗?没人应声,于是大家就对大人们的话产生了怀疑,对鬼魂的说法也不觉得可信了。有一男孩说:可能是鬼魂也有好坏,鬼魂害怕抗日英雄的英魂,不敢作乱了。这一说法,得到我们一致的认同。 二十多年后,我给小儿讲了童年的故事并告诉他此山曾是战场,小儿持怀疑态度,非要亲自去认定一下。在山顶上,他看到了破碎的碗片,废弃的石碾,倒塌的院墙等等,才吐出一句:看来还真打过仗啊!看到他惊奇的样子,我想到了那句话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那曾经的一切,对于他,的确是太遥远了,以后我要多给他讲讲这方面的故事。 其实,在我们岱崮曾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。最著名的莫过于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了。1943年11月1日,日伪军1万余人合击沂蒙山抗日根据地,我军指战员们依托山崮天险沉着应战,当地民众也送粮送水,支援守崮战斗。经过15天的浴血奋战,胜利地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,参战将士被授予“岱崮连”称号。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,还有第二次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、“龙须崮暴动”等,我就不一一赘述了。 我的故乡板崮山,它曾是抗日战争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之一,虽然它不像“孟良崮战役”那样惊天动地,也不像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那样轰轰烈烈,却随时随地地削弱了鬼子的力量。因为这些山崮的易守难攻,让鬼子们胆战心惊、四面楚歌,以至于屡次错失战机,这样一来,就更加快了我军胜利的步伐。从这一点上来说,板崮山、大崮、龙须崮等,都曾经是抗日英雄并肩作战的“战友”!今天,这些崮们经受了几十年风雨的洗礼,依旧赫然地屹立着。 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,如果没有英雄们的流血牺牲,哪来我们今天的幸福呢?英雄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,在他们为之战斗的地方,子孙后代们正奋斗着、努力着,把他们的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。人们越来越好的生活,也许可以告慰那些逝去的英魂吧!我们--这些英雄的后辈们,除了把家乡建设得更好,别无选择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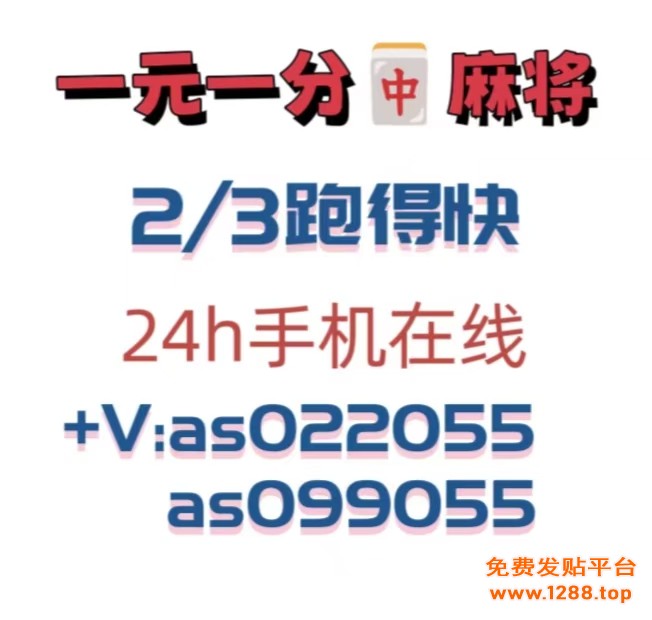 我在家的时候,我指的是我小学至中学这一段时间。家里经常生病的有两个人,一个是我奶奶一个就是我。我奶奶人老多病,是正常现象,而我年小多病,与体弱有关。母亲生我那年,刚好四十岁,老来得子,想着法子吃点补的,听人家说云南白药掺进母鸡汤里煲吃了补血。结果吃多,虚火内炽,脸色潮红,浑身像高烧的一样,胃口很差,就又按土郎中黄三的说法,吃了朱砂、黄连、地黄、当归、甘草五味药,败了虚火,安了神。可是,我遭了罪,先是跟着上火,然后就是泄个不停(吃奶故)。从此落下病根,平时虚火旺炽,胃口差,一着凉就会闹肚子。那时,家里的药罐子经常是满的,炖完奶奶的药汤就轮到我的了。黄三的药铺里多的是黄连,我买的多的药就是黄连和熟地,光吃黄连伤脾胃,加点熟地就好了。黄三大名我不清楚,知道他家是郎中世家,他父亲传给了他,因为他的两个哥哥都不肯学做郎中。黄三就成了江夏堂的继承人,这里需要交待的是,江夏是黄姓宗祠号,药铺起了××堂,是传统的习惯。 我低着头,不敢往前看,我在心里祈求老师不要再打他了。我只感觉到我恨自己,可是也恨他!我恨他不该那么倔强!我在心里说:你在地上跪一会,老师消了气不就没事了嘛!为什么偏象是头上长角了似的! 几个老外在翻译的带领下,走进这个院子,和我们一起看着朱红的大门,看着照壁上的图画。这些画源自哪个年代,已无从考据,只是孔子后裔的诸多故事,被日益生动地流传下来。那些老外一付虔诚的样子,认真地看,似懂非懂地听。我在怀疑他们的同时,又谴责了自己的浅薄。倘若我站在卢浮宫,是不是也被人称为槛外人?但凡是跨进这个大院的人,是怀着对孔子及其后人尊崇之心的。一种潜在的隐秘的文化纽带,把不同地方、肤色、语言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。他或她,还有我,在这个院子中静气屏息蹑足行走。先人早已不在,但不灭的灵魂在文化的时空中漫游。如果我们愿意想象,孔子的后人,在这里或那里看书、著书,烟火气息的生活。夜晚,一豆灯火之下,他们把头勾得很低,在书简之中,写下自己的思想。一些明明灭灭、虚虚实实的故事,在这里展开,让我迷惑。是的,迷惑。这种迷惑是因了时空的阻隔,而这种迷惑却因着特殊的地方,有了不可辩驳的可能性。这就是这个院子不断吸引人前来的魅力所在。 《美文》,1992年9月创刊,创刊时为韵文季刊,2001年兴盛为半季刊。下半季刊是“妙龄韵文”,公布中弟子韵文大作。《美文》有17篇大作收入国度成天制国学语文讲义和课本。个中有15篇为中弟子作家。 />英雄崮 在沂蒙山区,有很多形状特殊的山,这些山山峰陡峭,但山顶浑圆,地貌学上称“方山”,俗称崮。沂蒙山区有著名的72崮,其中我们蒙阴就有36座,而我的老家在一个偏远的山镇--岱崮,此地更因崮多而闻名。 我的童年就是在一座崮下度过的,那山崮的名字叫板崮。小时候,我经常和小朋友们去爬山。山就在我们家门口,又不是太高,一天一个来回也黑不了天,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壮举了。因为老人们常讲,板崮山曾是抗日根据地,那里死过好多革命战士、逃难的老百姓,也有被打死的日本鬼子、汉奸,特别是山头上和山洞里,曾经血流成河,所以传说那里有许多鬼魂,小孩子去了,会做恶梦的。我们几个女孩子从没有进过山洞,据说那就是当年的防空洞。有一次,几个胆大的男孩偏不信邪,点着松枝,吆三喝四地像英雄一样地走进去,不知谁在里面尖叫了一声,他们就风一样地跑出来,出来就笑作一团,说是什么也没看到。 这小小的恐惧很快就过去了。女孩子走那条陡窄的小路爬到山顶,男孩子就从比较容易爬的地方攀岩上去,也有爬不上去的,就成为大家的笑柄。山顶上有倒塌的房子,有的墙体还残破地站立着,大人们说的没错,的确是有人住过。“看!”谁又发现了几块黑瓷碗片,这又证实了山顶上住人的可能性,也让我们想起了那个洞和鬼魂的传说,还真有些害怕,于是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走到离洞远一点的地方玩。我们经常在这里玩打仗的游戏,体验一下“战争”的感觉。第二天我们见面的时候,第一句话就是问做恶梦了吗?没人应声,于是大家就对大人们的话产生了怀疑,对鬼魂的说法也不觉得可信了。有一男孩说:可能是鬼魂也有好坏,鬼魂害怕抗日英雄的英魂,不敢作乱了。这一说法,得到我们一致的认同。 二十多年后,我给小儿讲了童年的故事并告诉他此山曾是战场,小儿持怀疑态度,非要亲自去认定一下。在山顶上,他看到了破碎的碗片,废弃的石碾,倒塌的院墙等等,才吐出一句:看来还真打过仗啊!看到他惊奇的样子,我想到了那句话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那曾经的一切,对于他,的确是太遥远了,以后我要多给他讲讲这方面的故事。 其实,在我们岱崮曾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。最著名的莫过于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了。1943年11月1日,日伪军1万余人合击沂蒙山抗日根据地,我军指战员们依托山崮天险沉着应战,当地民众也送粮送水,支援守崮战斗。经过15天的浴血奋战,胜利地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,参战将士被授予“岱崮连”称号。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,还有第二次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、“龙须崮暴动”等,我就不一一赘述了。 我的故乡板崮山,它曾是抗日战争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之一,虽然它不像“孟良崮战役”那样惊天动地,也不像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那样轰轰烈烈,却随时随地地削弱了鬼子的力量。因为这些山崮的易守难攻,让鬼子们胆战心惊、四面楚歌,以至于屡次错失战机,这样一来,就更加快了我军胜利的步伐。从这一点上来说,板崮山、大崮、龙须崮等,都曾经是抗日英雄并肩作战的“战友”!今天,这些崮们经受了几十年风雨的洗礼,依旧赫然地屹立着。 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,如果没有英雄们的流血牺牲,哪来我们今天的幸福呢?英雄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,在他们为之战斗的地方,子孙后代们正奋斗着、努力着,把他们的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。人们越来越好的生活,也许可以告慰那些逝去的英魂吧!我们--这些英雄的后辈们,除了把家乡建设得更好,别无选择!
我在家的时候,我指的是我小学至中学这一段时间。家里经常生病的有两个人,一个是我奶奶一个就是我。我奶奶人老多病,是正常现象,而我年小多病,与体弱有关。母亲生我那年,刚好四十岁,老来得子,想着法子吃点补的,听人家说云南白药掺进母鸡汤里煲吃了补血。结果吃多,虚火内炽,脸色潮红,浑身像高烧的一样,胃口很差,就又按土郎中黄三的说法,吃了朱砂、黄连、地黄、当归、甘草五味药,败了虚火,安了神。可是,我遭了罪,先是跟着上火,然后就是泄个不停(吃奶故)。从此落下病根,平时虚火旺炽,胃口差,一着凉就会闹肚子。那时,家里的药罐子经常是满的,炖完奶奶的药汤就轮到我的了。黄三的药铺里多的是黄连,我买的多的药就是黄连和熟地,光吃黄连伤脾胃,加点熟地就好了。黄三大名我不清楚,知道他家是郎中世家,他父亲传给了他,因为他的两个哥哥都不肯学做郎中。黄三就成了江夏堂的继承人,这里需要交待的是,江夏是黄姓宗祠号,药铺起了××堂,是传统的习惯。 我低着头,不敢往前看,我在心里祈求老师不要再打他了。我只感觉到我恨自己,可是也恨他!我恨他不该那么倔强!我在心里说:你在地上跪一会,老师消了气不就没事了嘛!为什么偏象是头上长角了似的! 几个老外在翻译的带领下,走进这个院子,和我们一起看着朱红的大门,看着照壁上的图画。这些画源自哪个年代,已无从考据,只是孔子后裔的诸多故事,被日益生动地流传下来。那些老外一付虔诚的样子,认真地看,似懂非懂地听。我在怀疑他们的同时,又谴责了自己的浅薄。倘若我站在卢浮宫,是不是也被人称为槛外人?但凡是跨进这个大院的人,是怀着对孔子及其后人尊崇之心的。一种潜在的隐秘的文化纽带,把不同地方、肤色、语言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。他或她,还有我,在这个院子中静气屏息蹑足行走。先人早已不在,但不灭的灵魂在文化的时空中漫游。如果我们愿意想象,孔子的后人,在这里或那里看书、著书,烟火气息的生活。夜晚,一豆灯火之下,他们把头勾得很低,在书简之中,写下自己的思想。一些明明灭灭、虚虚实实的故事,在这里展开,让我迷惑。是的,迷惑。这种迷惑是因了时空的阻隔,而这种迷惑却因着特殊的地方,有了不可辩驳的可能性。这就是这个院子不断吸引人前来的魅力所在。 《美文》,1992年9月创刊,创刊时为韵文季刊,2001年兴盛为半季刊。下半季刊是“妙龄韵文”,公布中弟子韵文大作。《美文》有17篇大作收入国度成天制国学语文讲义和课本。个中有15篇为中弟子作家。 />英雄崮 在沂蒙山区,有很多形状特殊的山,这些山山峰陡峭,但山顶浑圆,地貌学上称“方山”,俗称崮。沂蒙山区有著名的72崮,其中我们蒙阴就有36座,而我的老家在一个偏远的山镇--岱崮,此地更因崮多而闻名。 我的童年就是在一座崮下度过的,那山崮的名字叫板崮。小时候,我经常和小朋友们去爬山。山就在我们家门口,又不是太高,一天一个来回也黑不了天,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壮举了。因为老人们常讲,板崮山曾是抗日根据地,那里死过好多革命战士、逃难的老百姓,也有被打死的日本鬼子、汉奸,特别是山头上和山洞里,曾经血流成河,所以传说那里有许多鬼魂,小孩子去了,会做恶梦的。我们几个女孩子从没有进过山洞,据说那就是当年的防空洞。有一次,几个胆大的男孩偏不信邪,点着松枝,吆三喝四地像英雄一样地走进去,不知谁在里面尖叫了一声,他们就风一样地跑出来,出来就笑作一团,说是什么也没看到。 这小小的恐惧很快就过去了。女孩子走那条陡窄的小路爬到山顶,男孩子就从比较容易爬的地方攀岩上去,也有爬不上去的,就成为大家的笑柄。山顶上有倒塌的房子,有的墙体还残破地站立着,大人们说的没错,的确是有人住过。“看!”谁又发现了几块黑瓷碗片,这又证实了山顶上住人的可能性,也让我们想起了那个洞和鬼魂的传说,还真有些害怕,于是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走到离洞远一点的地方玩。我们经常在这里玩打仗的游戏,体验一下“战争”的感觉。第二天我们见面的时候,第一句话就是问做恶梦了吗?没人应声,于是大家就对大人们的话产生了怀疑,对鬼魂的说法也不觉得可信了。有一男孩说:可能是鬼魂也有好坏,鬼魂害怕抗日英雄的英魂,不敢作乱了。这一说法,得到我们一致的认同。 二十多年后,我给小儿讲了童年的故事并告诉他此山曾是战场,小儿持怀疑态度,非要亲自去认定一下。在山顶上,他看到了破碎的碗片,废弃的石碾,倒塌的院墙等等,才吐出一句:看来还真打过仗啊!看到他惊奇的样子,我想到了那句话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那曾经的一切,对于他,的确是太遥远了,以后我要多给他讲讲这方面的故事。 其实,在我们岱崮曾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。最著名的莫过于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了。1943年11月1日,日伪军1万余人合击沂蒙山抗日根据地,我军指战员们依托山崮天险沉着应战,当地民众也送粮送水,支援守崮战斗。经过15天的浴血奋战,胜利地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,参战将士被授予“岱崮连”称号。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,还有第二次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、“龙须崮暴动”等,我就不一一赘述了。 我的故乡板崮山,它曾是抗日战争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之一,虽然它不像“孟良崮战役”那样惊天动地,也不像“南北两岱崮”战役那样轰轰烈烈,却随时随地地削弱了鬼子的力量。因为这些山崮的易守难攻,让鬼子们胆战心惊、四面楚歌,以至于屡次错失战机,这样一来,就更加快了我军胜利的步伐。从这一点上来说,板崮山、大崮、龙须崮等,都曾经是抗日英雄并肩作战的“战友”!今天,这些崮们经受了几十年风雨的洗礼,依旧赫然地屹立着。 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,如果没有英雄们的流血牺牲,哪来我们今天的幸福呢?英雄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,在他们为之战斗的地方,子孙后代们正奋斗着、努力着,把他们的梦想一步步变成现实。人们越来越好的生活,也许可以告慰那些逝去的英魂吧!我们--这些英雄的后辈们,除了把家乡建设得更好,别无选择!